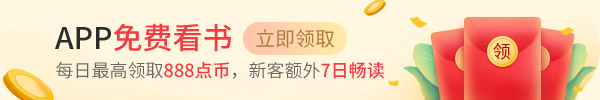打马从敖宁身边经过,敖彻的黑瞳从眼角淡淡扫了她一眼,又流转回去。
敖宁站在那里,一瞬间,热泪盈眶。
敖彻从她身旁飞驰而过,再不看她。
紧随敖彻身后,一队骑兵赶来,与那些土匪厮杀起来。
敖宁呆呆的看着最骁勇的那个身影,一瞬都不舍得挪开视线。
敖彻抽出长剑,所斩之处皆是一剑毙命,绝不拖泥带水。
敖彻从小便极有领兵打仗的天赋,很得父亲器重。
不仅如此,敖彻行事还非常谨慎严苛,治下严明,他带的兵,从来都是最训练有素,英勇善战的。
这个十年后威名赫赫杀伐果决的大人物,早就已经有了能成大事的风骨,可她却从未发觉。
敖宁忽然顿了顿,十年后,敖彻会成为什么大人物来着?
她怎么想不起来了?
摸了摸头上的包,在冰面上磕的这一下子,把她的许多记忆都磕没了。
罢了,他成为谁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还好好的活着。
那群土匪很快便被剿杀,敖彻清点了一下之后便准备收兵回营。
敖
敖宁回过神,开口要叫他。
却有一道剑风朝她袭来,接着,凉凉的剑刃便贴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三小姐开口之前,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小命。
敖彻此刻看敖宁的眼神,比看那些土匪还要阴沉。
敖彻看那些土匪是冷漠,看她却是厌恶。
敖宁心知,他之所以这般对她,是因为她一直以来伤他太深,她依稀记得,曾经的她和敖彻见面,轻则斥骂,重则喊打喊杀。
曾经的敖宁,但凡提起敖彻,都是恨不能将他杀之而后快。
敖彻自然不会忍气吞声,每每被敖宁欺辱,必定都会与她针锋相对,剑拔弩张,最后他们两个会闹个两败俱伤,谁都讨不到好。
如果不是因为敖宁仗着自己是威远侯的嫡女,敖彻最终也不会被她逼到挑断手脚筋,武功全废,还被赶出家门的地步。
曾经的敖宁容不下他。
他一定是恨她的。
敖彻肯定以为她开口又要对他数落折辱,所以才率先拔剑逼她住口。
敖宁心中愧疚,扬起小脸,甜甜的唤了一声:二哥。
敖彻是父亲从外面带回来的孩子,按年纪,她得叫他一声二哥。
她这一声二哥温柔甜腻,叫旁边收拾战场的士兵都惊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三小姐可从不这么叫他们将军的,今日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?
敖彻骑马的身影狠狠一僵,深邃的眼中渐渐升起诧异,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敖宁从不会如此亲昵的唤他。
从前,她都唤他野种。
叫我?
敖宁点了点头,推开他的剑,小跑着到他的马旁边,笑着看他:是啊,二哥。
二哥,你能带我回府吗,这山高路远的,我一个人害怕。
敖彻嗤笑:平日牙尖嘴利恨不得将我诛之后快的三小姐,竟会害怕?
敖彻再度将那凉飕飕的剑搭在了她的脖子上:与其带你回去,倒不如将你就地斩杀,回去我就跟侯爷说,你回府途中遭遇土匪,我赶来时你已被杀害,只剩一具尸体。这样,我便能一直过清静日子了。
敖宁瑟缩了一下,她知道,这种事他做得出来。
他是天底下独一个敢百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大人物,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,与他为敌的没有一个可以善终。
更何况现在的他那么恨她,这种事他不仅做的出,而且会做的非常干净利索。
敖宁不敢挑战他的底线,她只想努力缓和她与敖彻的关系。
扬起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,敖宁可怜兮兮的看着他。
二哥,你要是想杀我,就不会在我落水时救我了。我知道你肯定舍不得让我死的,你不要把我丢在这里,若我再遭遇什么歹人可怎么办?
敖彻的剑尖挑起她的一缕青丝,轻轻的在她细白的脖颈间搅弄,眼中满是讽刺:可若是我带你回去,你翻脸不认人,去侯爷面前告我一个带兵不利,辖地之中竟有匪徒猖獗之罪,我岂不是白当了好人?
毕竟,这种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敖宁只觉得心里一酸,原来她不分青红皂白的诬陷敖彻,已经很多次了吗?
敖宁并拢三指对天发誓:二哥,我发誓,从今往后,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,若我食言,必叫我受乱刀加身之刑,不得好死。
敖彻冷笑:这种赌咒,你当我会信?
敖宁表情认真:不管二哥信不信,我信。我曾经便是深深的伤害过一个人,所以最后,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,以至于最后,遗憾终生。
所以,我是很认真的对二哥发誓,不论前尘如何,希望二哥可以信我一次。
敖宁的眼中似是有水波,盈盈的看着敖彻,直将敖彻看的深吸了一口气。
敖彻气息沉了沉,终是对手下的兵士开口:给她让出一匹马。
谢谢二哥!
敖宁欢欢喜喜旁边人递过来的缰绳,翻身上马,又叫一个兵士帮忙把扶渠抬到她的马背上。
还没坐稳,就听敖彻在旁冷飕飕的开口:另外,我倒是想问问,三小姐在家把我当成死敌,在外竟宣扬我是你夫婿?